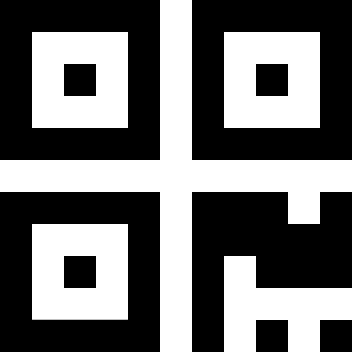公開組文藝類 鼓勵奬
《澳門短篇小說選》讀後
梁佐權
《澳門短篇小說選》(下稱“短選”)有廿八篇內容及形式各異的作品,要在一篇短文中逐一議論,是有其局限的,也難於談得透徹。
因為,這本“短選”裡的作品,表現手法頗為多樣化。從傳統現實主義的人物寫眞講故事方式,到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大膽想像,給予讀者自由想像的空間,至魔幻寫實主義的虛實並存,眞假難分。此外,又有一些“通俗”型的科幻小說,如胡根的《格洛卡男爵墓地》和勁夫的《死亡的永生》,都能在狀若“通俗”中利用這種吸引讀者興趣的體裁,宣示某些嚴肅的啓示。
不落俗套,變化瑰奇一直是短篇小說追求達到的境界,讀了之後,令人有拍案稱奇之感。
綜觀不少當代華文小說,傳統現實主義的成規範典還是溝通讀者的策略和契約,依然是多數作家自願遵守的創作“遊戲規則”,在人物塑造和情節方面,也還執着於文字世界與外在現實的等同。因此,在創作素材的選擇上,當前社會風氣和人的遭遇自然成為重點。“短選”中的小說,約有廿篇是直接反映澳門的人和事,而且都各具吸引讀者閱讀的藝術功力,令人讀後有盪氣迴腸或諫果回甘的不同程度反應。以下是其中一些有代表性作品的簡介:
九五年澳門文學奬冠軍梁淑淇的《等》可說是其中的傑作之一,是寫一個少年坐牢十年後出獄去約見女友,在餐廳等了老半天,他最後雖然親手接了女友的結婚請帖,但他終於因為巧遇那位在那間餐廳等了兒子十年的老婦而更為痛悔,原來他自己正是當年殺了老婦愛子的兇手。
這樣看來,現實主義小說並非過時,反而繼續是小說創作的永恆主流。假如自西方十九世紀小說叙述模式轉化過來的現實主義框架,從“五四”以來已成為絕大多數小說家受歡迎的原因,那麼,我們可以預料,剛出版不久的“短選”也將反映出它蘊含着多少藝術魅力,因而讀者對其中的故事和人物會感到熟悉和共鳴。
又例如,余行心的《快活樓》雖然是寫三十年代的賭場和賭徒的故事,但它依然具有很大的可讀性,至今依然會給讀者帶來啓迪。
林中英、勁夫和周桐等人的幾篇以家庭問題為題材的小說,用各個不同角度剖析了近年不少家庭的現實狀况和存在的問題,同時,也反映了整個社會風氣及其他因素如何影響了夫妻之間的愛情觀。其中,給筆者感受較深的《因我曾選擇過》,由於其內涵不是一般化,佈局新穎,心理刻劃細膩可信,加上結局別樹一幟,可引起讀者想像或不禁向自己提問:“假如我是小說主角,我會怎麼辦?”的效果。
同樣,前輩作家魯茂的《似花非花》是寫一個女秘書對其上司的色誘故事,其結局是有點出人意表,那個坐懷不亂的上司忠於髮妻的正面形象令人激賞。
追求讀者認同及情感投入是現實主義作品的兩大要求,為了滿足讀者對人間世事的求知慾,“短選”中的十四位澳門作家眞箇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雖然有老、中、青年齡之別,但他們的目的都是為了給建設澳門文學大廈獻上一磚一瓦而辛勤勞動。從“短選”各作品的字裡行間,筆者可感受到他們的求新、求變的意志及其可觀的現有成就。
當然,“短選”也包括葡藉作者的兩篇有關澳門的翻譯作品。此外,本地華籍作家胡根的《海鷗》以獨特的典型體現澳門特色的題材,運用細緻而具體的筆觸,刻劃出澳門中葡共處的人物性格。其寫作特點與前述筆者對林中英小說的看法類似,相信都能吸引讀者投入欣賞。
總之,“短選”基本上反映了澳門人各個層面的部分生活故事,令我大開眼界,並感到如果對它錯過閱讀機會,實在可惜。
因為始終抗戰時期的澳門小說創作,至今僅僅一代人的光景,能夠出版這一本珠玉紛呈的短篇精選,那是上一代人不能想像的。
近百年來的世界文學可謂多姿多采,百家爭鳴。如果說,它可被喻為一部交響樂,那麼,澳門的文學就是躍動其間的一個音符。由於澳門文學起步較遲,“短選”選取了幾篇較為“難明”的非現實主義小說,也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如果小說題材過份“西化”,加上缺乏內在的解說或差距過大,恐會產生“曲高和寡”的效果。例如梯亞四篇小說的其中一篇《論一個關於命運(或者自殺)的格言》第二回。由幾個外國人(三島由紀夫、馬雅可夫斯基、湯因比、池田大作在七九七二──一九七三年期間交談“自殺”的“哲理之類”,筆者就有“雞肋”之嘆。(附註:“七九七二”應是手民之誤)。
六十年代後,法國反主流的新小說流派崛起,拉丁美洲的魔幻寫實主義及德國的“寓言式”極短小說,都相繼以繽紛歧異的實踐,動搖現實主義的一尊“霸權”,這本來是文學生命避免走向枯竭的嘗試,是好事。問題是,以現時澳門讀者的慣性反應及商品經濟市場規律而論,若太熱衷出版這類“大作”恐非時宜。
相關附件:![]() 《澳門短篇小說選》讀後感_梁佐權
《澳門短篇小說選》讀後感_梁佐權